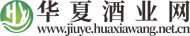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、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回忆,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有一个鄙视圈:黄埔系瞧不起杂牌军,杂牌军瞧不起“牛字号”,“牛字号”中“戴家班”瞧不起“CC”。
所谓“牛字号”,指的就是特务,“戴家班”指的是军统(保密局),“CC”就是二陈——中统(党通局、内调局)一直被陈立夫、陈果夫把控。
这些将军级战犯们互相撕咬,连善于交际的王耀武、沈醉也经常挨上几口,就更别说脾气古怪和暴躁的黄维、徐远举了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这些不同派系的将军们在枪炮轰鸣的战场上战败被俘,就把战场转移到了不见硝烟的功德林,在那里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串,拿队友当对手,唇枪舌剑争斗不休,有时候还抡拳头扇耳光打成一团,比如“牛字号”的董益三(军统局第四处少将副处长,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)就曾把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一耳光打懵,等黄维想起反击的时候,被大家七手八脚拉开按住了。
这些黄埔系、杂牌军、“牛字号”、“CC系”平日里鸡争狗斗,但是面对他们中的一些特殊人物,还是能步调一致表示藐视、唾弃的。
被绝大多数将军级战犯瞧不起的“同学”有很多,但是有三个军长,算是把“讨人嫌”发挥到了极致,大家在回忆录中,极尽冷嘲热讽,这跟他们的派系无关,实在是他们做出的事情令人难以接受。
沈醉性格比较圆融,一般不会说别人的坏话,但那个坏人要是表现实在太拙劣,他也不介意在回忆录中暗戳戳地嘲笑一番。
贪财、好色、虚伪之人,往往会被人瞧不起,尤其是在战争年代,这三种人带来的危害更严重,一旦被揭穿,就可能成为过街老鼠。
前一段时间有人撰文大吹《潜伏》中被代理抓起来的九十二军副军长杨文泉(瑔),说他如何“坚持”和“忠于老蒋”,实际上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一百多个将军,没有一个可能为老蒋“成仁”,战败后被俘后都比绵羊还乖,也没有一个敢对管理员大喊大叫,动手反抗的事情,他们在梦里都不敢想。
那个被吹成顽抗到底死不悔改的杨文泉,实际是很被“同学”鄙视的,鄙视的原因,就是那厮太好色,而且对自己的容貌实在是太上心了,即使成了战犯,仍然不忘整天“涂脂抹粉”。
正常的胭脂水粉搞不到,他就另想办法:他洗脸可以洗上十几二十分钟,洗完还得在脸上涂点雪花膏之类润肤的东西,最后才在发上抹点油脂——那是他冬天可以买到的防皮肤皴裂的蛤蜊油、甘油、凡士林混合物,真不知道他存那么多凡士林干什么,据说只有某种有特殊爱好的家伙才会常备那玩意。
这些能让杨文泉保持油头粉面的东西,味道肯定不会太好,所以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客气地嘲讽:“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,就总认为他不像个军人,满身香气扑鼻,而且还有点和古代文人陆机《赴洛道中》诗中描写的一样,有些“顾影自怜”那一股酸劲儿。总之,不是味道!成了战争罪犯,还一直保持着粉面油头,可能是闻所未闻吧!”
那“味道”,不是物理的,也不是化学的,而是骨子里透出的令人厌恶的气息,所以在整个功德林战犯管理所,也就是沈醉能捏着鼻子跟他说几句话,其他人都避之唯恐不及——这些吃过见过的将军们肯定不会对杨文泉有啥怪异想法,他们是怕杨文泉有了想法,那想法想想都能让人吐三天。
杨文泉在战犯管理所整天把自己打理得油头粉面怪味熏人,比落入皇太极手里的洪承畴还“注意形象”,指望这样的人有骨气,那些“作家”可能也是被凡士林蒙了心。
杨文泉之所以有这样奇葩的“喜好”,就是因为他好色,沈醉说“也是一种小小的病态心理反应”,还真没说屈了他:“他过去到一个地方,便极力追求当地的什么交际花、校花、名媛闺秀等一类在社会上有声誉的美人儿,直到最后结合。”
杨文泉从来都是毫不隐晦地告诉沈醉他始乱终弃的“妙招”:“一旦玩厌了想改改口味,只要几番争吵,一记耳光,对方马上就会同意离婚。过去排队没有排上的,立刻会欢天喜地地接收过去,一点没有麻烦。”
沈醉对妻子是比较忠诚的,所以他很是瞧不起杨文泉的做派,对杨文泉的下场也有些解恨和幸灾乐祸:“我越听越感到不是味儿,像杨文泉这种人已经当了囚犯了,还沉迷着旧日的罪恶。他统率的四川部队七十二军(戴笠坠机后,杨文泉被放了出来,晋升为七十二军中将军长、整编七十二师中将师长,估计是军火商孙女那十万银圆的嫁妆买来的结果)在山东战场被活捉时,是孤家寡人,没有带随军家属。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时,也从来没有听说他的家眷去看过他,这回可能是女方把他丢掉了。 ”
中将军长杨文泉好色,还有一个中将军长贪财,这个被沈醉笑为“牛虽丢,仍得捡回牵牛绳子;贪婪成性,军长仍爱小偷摸”的家伙,是“嫡系六十六军的军长,安徽合肥人”。
该军长之贪婪,在蒋军系统也算个极品:“他过去一直是个贪官,从他当连长起就吃缺。他带的一连兵,从来没有满员,这一方面是因常有开小差和病故的;另一方面是他有意不让满额,存心吃缺。由当连长吃几个到当营长是十几二十个,当团长、师长便越吃越多。当了军长,更可以大吃特吃了。”
沈醉在功德林见过这位六十六军中将军长,所以他肯定不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六十六军最后一任军长罗贤达——沈醉是1956年才从重庆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,所以他不可能见到活的罗贤达偷纽扣,罗贤达也不可能亲口告诉沈醉他的“偷论”:“牛虽丢了,也得把牵牛的绳子捡回来,总比空着手好一些。”
这个六十六军军长因为太贪财,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很不受同学待见的,他刚写了一首诗贴在墙报上,马上有十多个将军写文章骂他,最后骂得他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。
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,杜聿明、黄维等人都不太喜欢钱,王耀武是做买卖赚钱而不吃空饷,那种“喝病血”的将军,走到哪里都会成为过街老鼠:要不是你们贪得无厌,弄得军心涣散,我们还至于在这里见面吗?
六十六军军长偷纽扣被功德林传为笑话,七十二军军长把自己活成了笑话,而第六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兵团司令部代参谋长娄福生,则让沈醉这个乐天派也笑不出来:此人假装积极,一向损人利己,居然只比沈醉晚一年特赦。
前面两个军长贪财好色令人不齿,这位副军长则是连沈醉都不得不表示“佩服”:“一是脸皮厚,可以取别人劳动成果为己有或分别人一半为己有;二是外表装得比任何人都卖劲,实则出力甚少,而喊得最响;三是有管理员在场是真卖力,遇到没有管理员在场就借机会少干或不干。”
沈醉已经够精明的了,但是娄福生比他还精明,沈醉和他“搭档”,只能吃亏,半点便宜都占不到。
两人最初的合作始于洗被套,战犯们两个月才洗一次被套,那肯定是不太好洗的,娄福生看新来的沈醉年轻力壮,就主动要求合作:沈醉负责搓洗,他负责交给洗涤组长验收。
沈醉累得汗流浃背,受表扬的却是娄福生,沈醉又好气又好笑,也想找个机会把搞他一下,结果还是没算计过娄福生。
当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时候会组织“学员”们到农场参加一些劳动,沈醉一开始还沾沾自喜:“到农场去劳动,我认为娄福生再也钻不到空子了。这是要硬碰硬去干的,无巧可取。”
没想到娄福生又用自己的精明,摆了沈醉一道。
当时战犯们的劳动强度不是很大,到农场劳动,就是摘果子,不但可以当场饱吃一顿,还可以悄悄带点回去。
沈醉武功不错,从小就爱爬树抓鸟捕蝉,爬树的本领也高人一筹,三五米的果树三下两下就能爬到树梢。
沈醉矫健的身手,自然逃不过“老搭档”娄福生的眼睛,他再次跑过来跟沈醉合作:沈醉在树上摘下果子往下扔,娄福生在地上捡起来装筐送到集中地,然后娄福生又因为“摘”得最多而受到了表扬,沈醉则只能在树上苦笑。
沈醉笑而不言,但是“同学”们和管理员眼睛是雪亮的,娄福生一贯投机取巧,最后还是穿了帮,不但被大家藐视,还被管理员批评了一顿。
那是在农场修路的时候,大家一起拉石磙。有人肩膀都被麻绳勒肿了,娄福生却连一点汗都没出:“这一次,娄的花招被同他在一起拉磙的一位管理员发现了,当面批评他:‘叫得最起劲,拉得最不起劲,有时连绳子都没有拉直。’从那以后,他那一套投机取巧的办法便被戳穿了,再也没有受到过表扬。”
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的三个“讨人嫌军长”盘点完了,好色的军长杨文泉没等特赦到他就病死了,假装积极的军长娄福生特赦后很少有人提及,只有那个安徽合肥籍的六十六军军长姓甚名谁,至今仍然是个谜,用王耀武的话来说,那就是“知不道”。
其实像这样贪财、好色、虚伪的军长,在老蒋的军队中比比皆是。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,他们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恶习不改,弄得人嫌狗不待见,老蒋对这样的人委以重任,败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,读者诸君看了这三位军长的表现,肯定也有话要说:在您看来,跟这三个战犯军长一样的三种人,哪一种最令人厌恶?那位丢牛也要捡绳子的军长,您知道是谁吗?